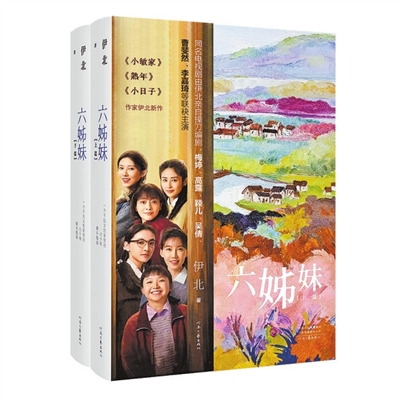
□宗承灏
伊北的长篇小说《六姊妹》以安徽淮南为地理坐标,以何家三代女性的命运为线索,铺陈了一幅跨越60年的中国社会变迁图景。这部近百万字的鸿篇巨制,既是一部平民家族的史诗,也是一部女性觉醒的成长录。
《六姊妹》是家国同构的历史书写。叙事起点始于20世纪60年代,何常胜一家从扬州江都迁至淮南,成为新中国工业化浪潮中的第一代移民。这一家庭迁徙的抉择,暗合了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何家“求子不得”的命运,成为传统宗族观念与现代化进程碰撞的隐喻。小说通过何家六姊妹的出生与成长,串联起三年困难时期、改革开放、下岗潮、下海经商等重大历史事件,展现出个人命运如何被时代车轮裹挟前行。
何家的特殊性在于其“无男丁”的性别结构,这一设定颠覆了传统家族叙事的父权框架。何常胜的“求子执念”与最终“女性当家”的结局,象征了从宗法社会向现代家庭伦理的过渡。小说中,何家老太太以智慧和韧性维系家族,而六姊妹的分家、争斗与和解,揭示了传统大家庭的解体与小家庭独立化的必然性。当经济独立取代血缘依附,家族凝聚力逐渐让位于个体主义。
本书是一部时代儿女的精神成长史。我与作家相识有年,他的身上有迥然不同的两种特质,一种是江南人的温润儒雅,一种是淮南人的简单直接。《六姊妹》这部小说,两种性格交替附着于他的笔端,塑造了性格迥异的六姊妹:老大何家丽是家族责任的承担者,性格坚韧,牺牲自我,是“中国式”长女的代表形象;老二何家文聪慧却“不争不抢”,成为女性独立意识的缩影;老三何家艺是争强好胜的叛逆者,从商海沉浮中完成自我价值的重构;老四何家欢是知识改变命运的践行者,其牢狱之灾暗喻体制转型的阵痛;老五刘小玲是混沌中的觉醒者,历经婚姻失败的坎坷完成自我救赎;老六何家喜是自私跋扈的“反传统者”,最终在疾病中领悟亲情真谛。
这六重镜像,折射出不同代际女性的生存策略与精神困境,既有对传统性别角色的突围,也有对现代性代价的反思。小说中,何家老太太与儿媳刘美心的关系构成另一重张力。老太太的持家智慧与刘美心的偏执自私形成对比。以上这些“母系叙事”,不仅颠覆了父权制家庭的话语结构,更暗示了女性主体意识的代际传递。
这本书的叙事策略,在烟火气中有史诗品格。伊北采用传统线性叙事,以时间顺序串联60年的家族史。这种“笨拙”的叙述方式(伊北自评)强化了历史的厚重感。作为淮南籍作家,伊北在小说中大量使用江淮方言,细致描写淮南煤矿城市的文化特质。地域性书写不仅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性,更将家族故事升华为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从这一点上说:“《六姊妹》是淮南的三代女性故事,更是中国工业城市的微观史。”伊北自称“以喜剧形式写市井小人物的顽强”,但文本中处处可见悲剧性隐喻。这种“笑中带泪”的美学风格,既继承了《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带有美国小说《小妇人》式的女性温情。
《六姊妹》的价值在于其“以小见大”的叙事野心。通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变迁,它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伦理的瓦解(如家族凝聚力的衰退)、性别观念的转型(如女性从附属者到主导者)以及个体与时代的共生关系。这种书写,既是对《红楼梦》等古典世情小说的致敬,也是对当代“新写实主义”的拓展。《六姊妹》客观上成为一部女性觉醒的典型文本。六姊妹的多元命运,打破了“贤妻良母”的单一模板,尤其是何家艺的商业突围与何家欢的知识抗争,展现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小说对男性角色的弱化处理,也暴露了性别叙事的某种失衡。
作为一部“雅俗共赏”的作品,《六姊妹》在各大阅读平台的高热度与影视化,成功证明了其大众吸引力。《六姊妹》的终极追问是“家为何物”。伊北以一部平民史诗完成了对“家”的解构与重构。在这个意义上,《六姊妹》不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一面映照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