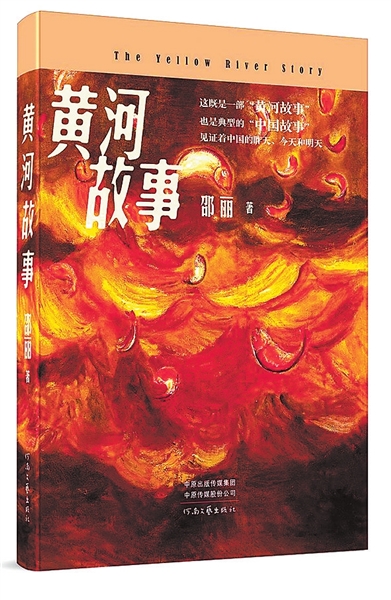
□魏华莹
2020年,邵丽在《人民文学》第6期发表《黄河故事》,后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是她较为明晰地树立起地域写作意识的作品。在自序中,她详细讲述了从儿时与黄河的交集,逐渐萌生的对黄河的情感,追溯了黄河的写作源流,以及不同时期作家在黄河书写中试图探寻的民族文化性格。小说中刻意将黄河岸边的故乡郑州与新兴城市深圳双城对读,也拉开了故事框架,融入作者对改革开放时代故土与异乡的文化反思。
《黄河故事》一书序言梳理了黄河故事的历史文脉,从《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李白“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再到新中国作家李準的《大河奔流》《黄河东流去》,黄河一直是文人墨客的浓墨重彩所在。李準的《黄河东流去》重在表现中国文化以及从苦难中挖掘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文化根脉,并为当下寻找精神图腾和栖息之地。在李準看来,正是黄河给了中原人热烈的性格。黄河给予不同时代的写作者讲述故事的背景和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邵丽的《黄河故事》,所接续的也是河南文学的重要传统,作品着重写出集体化时期和改革开放时代黄河岸边的故事,更直接映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原人民的生存史和发展史。
《黄河故事》中,母亲需要稳定,需要长幼有序的尊严和面子,需要家要有个家的样子。父亲是破坏秩序的始作俑者。刚强倔强的母亲,一开始对公子哥般的父亲充满希望。认为他出身大家,见过世面,一定有主见、有魄力,没想到父亲干起事情来百无一用。父亲在母亲心中,是一种定格的毫无用处的形象,而在村人和子女的记忆中,却存在一个不乏温情的父亲。作者尝试打开历史,通过不同记忆和讲述建构一位缺席的父亲形象。代际差异的实质性内容,是社会文化特质而非其自然属性,父亲作为一位悲剧人物,既有个人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被禁锢的年代,释放本我的父亲没有任何的正面价值,只能徒自悲伤和找不到出路。
所以,在作品中,我们会看到母亲对于父亲不务正业的不满,对子女婚姻、工作问题的干涉,对体制人的羡慕与向往,以及固有的阶级眼光对子女的厚爱与歧视,造成的母亲与几个子女的紧张关系。但如果仅仅从时代因素来看,如何认识后面故事讲述中弟弟这个形象,也是如此的懦弱和发不出声音,也显示出作者对于男性话语和力量的并不信任。但是作品中还是写到父亲对二姐和“我”的温情与爱意,在子女心中的温暖形象,这些人类基本的情感和恒定的事物,才是打动人心之处。
还好,时代变化了,才有了“我”对家庭的背离和无限的可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有了子女们各寻出路以及“我”的崛起。作品将时代的差异性通过地理空间、双城故事的方式展现出来。郑州所在的家乡城市,代表了传统的文明和根脉,深圳代表了新兴的改革开放史。追忆、建构的父亲代表改革开放前的集体时代,我们当下的生活,则有着改革开放鼓励个人奋斗的时代气息。
母亲在深圳的楼顶上种满了荆芥、玉米菜、薄荷、小茴香,而我们的厨艺基因也有着遥远的家乡文脉。“我”家所在的黄河岸边,曾出过列子。列子的存在完成了与历史的勾连,“我”家天生的厨艺基因也许来源于此。
双城故事的对读,是发展的深圳的勃勃生机以及郑州的中原寻古的并置。中原的存在勾连起悠久的历史,以及文化的传承,深圳作为新兴城市,则体现出改革开放时代的活跃与光彩。似乎为了印证,作品还特意回顾父亲所处的集体时代,对于个人欲望的压抑。
而在场景还原的返乡之旅中,作者不断通过家族故事、打捞的历史记忆建构起郑州的文学地理与时代空间。父亲的特长在那个年代毫无用处。这不禁让人想起阿城的《棋王》、张贤亮的《灵与肉》等,对于口腹、身体之欲的极力书写成为禁欲时代人本欲望的张扬。再回到作品书写的年代,可以发现被集体压抑下的个性,成为被贬斥的另类存在,以及不得不以自我欲望和肉身消泯的方式结局。
作品尝试打开的,还是一部改革开放史。与家乡的姊妹兄弟们静止的没有流动的、沉浸在过去时光的缓慢日子不同,是“我”在异乡励志的奋斗史。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被寄予着“拆掉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期待,深圳的勃勃生机和记忆中家乡的荒凉成为一种参照。
市场经济时代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巨大差异,剧烈的城市文明形态变化集中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我”作为异乡人来到深圳后,和老板女儿任小瑜的交集,显示着巨大的时空错位。但“我”很快凭借个人奋斗融入了城市神话,适应了变动的社会秩序,收获了事业、爱情。
在“我”适应不断发展的城市文明形态过程中,既有着河南人朴实、勤奋的古风,也有着深圳新型社会重契约、守诚信的现代精神。家乡代表着稳定秩序,即便“我”再度返回,发现郑东新区的发展变化,仿佛再现了深圳。而在高歌猛进的新中国城市化运动中,“我”也在不断寻找缝合之处,寻找自我的价值归属与情感认同。自我与时代,通过家庭故事打开而又和解,母亲和“我”重新理解了父亲,也重拾返乡的愿望。
关于作家的写作姿态问题,洪子诚曾提出不同时代语境与创作者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环境更多是一种感伤姿态,对变革的渴望,对自我的认识和表现的渴望,自我意识开始崛起。到了90年代,作家、批评家共同有一种责任意识、使命感和文化自觉。新世纪以后,作家更多成为讲故事的人,故事中所蕴含的社会生活形态、文化背景、历史意识、人生意识成为重要的衡量层面。具体在邵丽的写作中,我们会发现她对黄河等故土的文化融入,和生活变迁的呈现,试图从文学地理上打开时代与人的关系。虽然,《黄河故事》中还掺杂了诸多姊妹的故事,其实作品还是不断寻求精神和解的故事,尽管带有成长经历的伤痕,带有巨大的地域文化差异,但终究都需要与历史中的自我和他人进行精神上的和解。在作者不断重返故乡、历史记忆,寻找父亲之旅中,也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社会动荡中个体与时代的发展史,那些无名的被压抑的父辈的命运故事,以及自我原乡与他乡的认知,其间所融入的文化精神、寻根意识,实现了与黄河故土的时代接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