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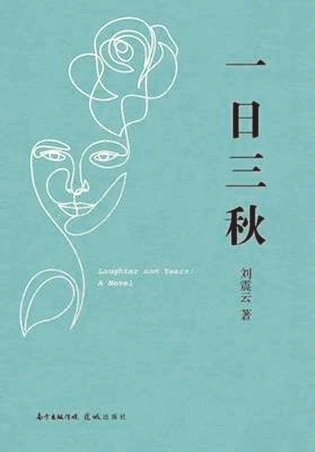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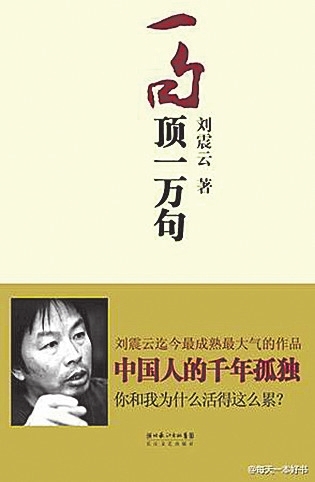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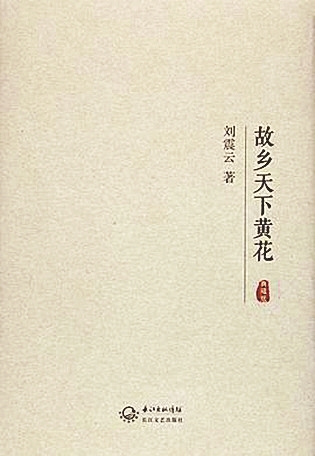
□赵梦颖
豫籍茅奖作家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经典过程中需要讨论的文学现象之一。在走向经典化的过程中,作家本人的经典意识和经典自觉,对作品本身的经典品格生成具有关键性作用。作家作品文学经典品格的追求和获得,最终能够推动文学作品走向文化高地。
在当代文学批评家当中,摩罗、吴义勤等大力呼吁要接受当代文学中经典的诞生。摩罗认为:“我们总是习惯于等到一个作家熬到90岁才称他为文学大师,或者等到他逝去若干年之后,才追封一个大师称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他写出了真正的好作品之后,及时地予以肯定和推重呢?”
刘震云作为豫籍茅奖作家,其作品不仅走向全国,也享誉世界,其对文学经典性品格有着自觉而强烈的追求,追求原创性、“写出事物的本质”、强调作家的“读者意识”、强调创作的超越性,这些文学创作追求让刘震云作品具备了鲜明的经典化品格。
刘震云是从河南延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作家。自1987年他以《塔铺》在当代小说界一鸣惊人,到2011年凭借《一句顶一万句》斩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我不是潘金莲》在国内外大热,近年力作《一日三秋》发表后引起了热烈讨论,刘震云小说创作的价值在国内得到认可,也让中国文学获得了国外赞誉。
1987年后,他开始发表《单位》《一地鸡毛》《官场》等小说,迅速迎来文坛关注。之后刘震云埋头6年写出了不为世人“接受”的《故乡面和花朵》。这部长达四卷200万字的大部头小说,刷新了小说字数纪录,天马行空似的叙事风格也让当时评论界无从言说。
刘震云说自己在《故乡面和花朵》中想要反思的是,一方面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语言的洪流是怎么淹没人、群体、生活的”;另一方面是结构的问题,或者说语言表象背后的生活逻辑问题成为他思考小说写作的新维度。《一句顶一万句》尝试进入中国底层人的心灵,发现这个人群的心灵孤独问题。小说采用传统话本小说“说书人”的叙述声口,书中出现了100多号人物,一个人物引出另外一个人物,每个人物的线头岔开又圆合,结构恢宏,想象瑰奇。小说的整个叙述盘根错节,枝蔓横生,呈现出底层社会民众群像众生的生活画卷和心灵龃龉。
《我不是潘金莲》有着最长的序言和最短的正文,序言用10余万字写农村妇女李雪莲的上访,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最后一章是正文,以8000字写主人公史为民“戏仿”的故事。通过这种“结构动力学”,呼应着刘震云“幽默”背后的“荒诞”本质。
《一日三秋》引入中国传统小说的“志怪传统”写当代的“延津故事”,结构上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小说戏里戏外、人间鬼神、上天入地、梦里梦外、逆向顺向,不拘一格又万流归一,结构上多重反复和环环相嵌,“笑话”在结构上的多重反复最终引出“笑话”是每个人“荒谬”的生存本质的哲学观的呈现。
刘震云认为:“作者的写作手段都是差不多的,真正的考验不在写作中,而是在写作前,在于你能不能从相同的生活中有不同的发现,就是作者的见识是否独特,凡是好作者,见识与其他人必然不同。”他不重复自己,而是追求和自己作品中的人物贴近,去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也总能在生活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道理”。这种追求原创性的品格,是他的创作走向经典化的重要动力。
刘震云追求写出生活的“真相”,写出事物表象下面隐藏的“道理”。小说《单位》把中国官僚体制中的利益分配、钩心斗角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异化勾勒得淋漓尽致。他对中国“单位”这一权力机制的解剖,是一种网状的写法,写出深陷在“网”中的人的无能为力。评论家石丛这样描述刘震云的变化:读过《塔铺》和《新兵连》,再读《单位》,我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作者有了一个观察世界的全新方式。不再把世界一分为二为对立的两极,不再从一个个人物身上去寻找“典型性”,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个别人物的命运,而是考察群体的生存状态。
在《单位》与《一地鸡毛》里,刘震云矛头指向的是作为制度化的官僚体制本身对人性的压迫。如陈晓明指出的那样:“刘震云试图运用‘反讽’去解开人类本性与制度化的存在结合一体的秘密。……人们自觉认同权力的结果,就足以使权力渗透我们每时每刻的生存。”陈思和指出:“自《单位》始,刘震云的小说自成一个‘神话’文本……它叙述的故事时空不一,但重复了同一的原型。原型包括了两个相反相成的模式,可用中国古代寓言来表达:‘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由此还派生出一系列亚模式。”刘震云的小说总是有着不一样的面孔,但实质上永恒的主题是对权力的书写,权力是其文学书写恒久的“神话”。
他写《单位》和《一地鸡毛》,把中国人生存的组织结构解剖得十分深刻,写《一句顶一万句》直接发现了中国人“千年孤独”的心灵“秘密”,他善于发现和捕捉生活中被人忽视或遮蔽的生存本相,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刘震云是和鲁迅一样追求思想性写作的作家,他的创作具有强大的思想性特质。
刘震云曾被称为“草根作家”,因为个人经历,刘震云的创作一直保持了对民间社会的亲近。他在采访中多次说到,他对小人物有感情,喜欢写小人物。“新写实”阶段,刘震云的创作在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上就有与“读者”的天然贴近,民间创作转型后,刘震云的创作者身份上更愿意转变为“倾听者”:“当我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写作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对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你要读懂他。”《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让我们看到了小人物的内心也是惊涛骇浪的,刘震云对这些底层普通人的心事的倾听,会让读者觉得亲近和温暖。
优秀的作家总是追求自己的作品能与不同时代的人对话,永远焕发着不同魅力。刘震云认为“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即作者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它又不是哲学,哲学是把世界说明白,文学恰恰不管世界能说明白的事儿,管的是世界说不明白的事儿,比如感情、人性”。文学需要达到哲学的高度呈现深刻,但文学与哲学不同,他的魅力就在于“说不明白”。
“看一个作家是不是大作家,主要应看他与人类的精神生活联系得有多深,或者说对这种联系揭示得有多深。落到实处来说,就是看他与他的民族、他的时代的精神生活联系得有多深,或者说对这种联系揭示得有多深。”刘震云的创作是民族精神生活的发现和书写显然已经具有“大家”气象,当一个作家的写作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时候,他的创作显然具有一种胸襟和气度,具有一种超越性视野。
刘震云的创作是河南作家群中实绩最为突出的一位,也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走向世界的一位。他的作品广泛传播到海外世界,在英语世界、法语世界、阿拉伯语世界等获得了高度的赞誉。作为当代已经和正在走向经典化的重要作家,对这一经典化的过程和规律进行研究,一方面不仅能够确立刘震云创作本身的价值,看到他创造乡土文学和中国经验的自觉,为河南文学创造新时代的文化高地提供经验;一方面也可以获取当代文学经典生成条件的新变化及一般规律,为河南作家在新时代下创造当代经典提供经验。
